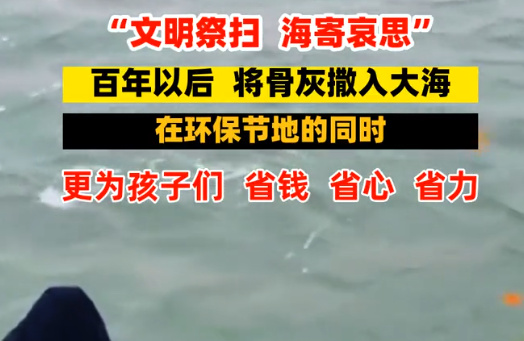清晨的海风裹着咸湿水汽,落在我指缝间的檀木骨灰盒上——盒身雕着浅淡桅子花,是爸爸找老木匠仿奶奶窗台上那盆花做的。昨天妈妈蹲在客厅擦了三遍,擦着擦着红了眼:“这盒子太新,妈肯定嫌硌得慌。
奶奶走前的晚上,意识模糊却攥着我手用气音说“丫丫,海”——我想起她去年秋天翻相册的样子,指着扎麻花辫站在礁石上的老照片笑:“你太爷爷说海里是归墟,想念的人都藏在里面。”她总说小时候跟着太爷爷赶海,天没亮就爬起来,摸满筐花蛤煮的汤鲜得能咽舌头,后来嫁去城里,每年清明都要回海边,说“海里有我半个魂儿”。
撒海选在农历十五,奶奶说过“十五的潮最稳”。凌晨四点的海边泛着淡紫光,爸爸把骨灰倒进她的蓝布围裙——口袋上有我小时候打翻酱油烧的补丁。妈妈往围裙里塞了把米(“妈饿过肚子,得带点粮”),又放了朵带露的桅子花。我们走到离海最近的礁石上,爸爸解开围裙系带,风忽然吹起来,骨灰顺着风丝儿飘下去,像奶奶晒在绳子上的被单,慢慢展开融进浪里。妈妈把桅子花轻轻丢下去,花朵打着旋儿沉底,像她生前弯腰捡花的样子。
“妈,这次换我们陪你赶海。”爸爸声音哑却带着笑。我想起小时候她攥着我手不让踩深水,自己往礁石缝里钻,摸出花蛤就举给我看,阳光照得她皱纹里都是笑。现在她终于能自由自在钻礁石缝了,不用再担心我摔着,不用急着回家做午饭,她可以在海里慢慢逛,累了就躺在浪尖晒太阳,像生前坐藤椅那样。

那天之后我总往海边跑。上周捡了个螺旋纹贝壳,像奶奶晒了太阳的手背,我把它放口袋里,走在沙滩上,海浪打湿裤脚——忽然想起她小时候抱我起来说“丫丫的小脚丫不能沾凉”。风里飘来桅子花香,不知道哪户人家种的,却像她凑在我耳边说“乖,奶奶在这儿”。

昨天清晨陪爸爸去看日出,太阳从海里浮起来时,他指着一团毛边云说“像妈织的围巾”——去年冬天她还在织米白色围巾,说要给我当新年礼物,没织完就住院了。风里的海味混着桅子香,我蹲下来蘸了点海水尝,咸咸的,像她做的咸菜。忽然听见有人喊“丫丫”,回头看没人,可风更暖了,像她的手摸着我头发。
原来撒海从不是“送走”,是把她送回最爱的地方。那些没说出口的想念、没做完的梦,跟着海浪在潮起时涌过来,在风过时绕着我转。就像爸爸说的:“妈从来没走,她只是换了方式每天陪我们看日出。”上周我在海边捡了个贝壳,放在枕头边,夜里听见海浪声,像她拍我后背哄我睡觉的节奏——她还是那个爱赶海的老太太,还是那个把我抱起来的奶奶,只是现在她的脚印藏在每一粒细沙里,笑声裹在每一阵风里,想念浸在每一滴海水里,在我想起她的每一刻,轻轻碰一下我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