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风掠过圆明园的断柱,我抱着相机站在海晏堂遗址前,忽然想起十年前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看到的那张褪色照片——1870年法国摄影师镜头里的海晏堂,两层汉白玉建筑雕梁画栋,正中央大喷泉喷着水柱,十二兽首整齐排列在两侧,牛首下巴的褶皱、猴首脸颊的酒窝都清晰得像能摸得到。照片右下角写着"圆明园最华丽的水法殿",可旁边注释刺痛人:"拍摄后十年,这里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"。
蹲下来对准眼前的断柱,这根柱子刚好是老照片里正厅的左柱。柱身缠枝莲雕刻还在,花瓣边缘被炮火熏黑,石缝里却钻着株新绿的小草。忽然懂了为什么大家爱拍海晏堂的图片——它们不是静止的风景,是时间叠起来的层。比如十二兽首,现在能看到的老照片里,马首鬃毛根根分明,可1860年后的残照里,那些位置只剩空洞的柱础,像诗少了最关键的字,让人心里发疼。
去年在档案馆查到1920年的海晏堂照片:西配殿只剩半面墙,柱础雕刻被炮火炸模糊,可墙角那丛二月兰开得旺盛。照片背面写着拍摄者的话:"废墟里的孩子,比花还好看"。原来海晏堂的图片从不是"悲剧标本",它记着繁华,也记着废墟里的生机;记着毁灭,也记着倔强的生长。就像现在眼前的断柱间,二月兰绕着石头开,风一吹,紫色花簇碰着古老的刻痕,像在和历史对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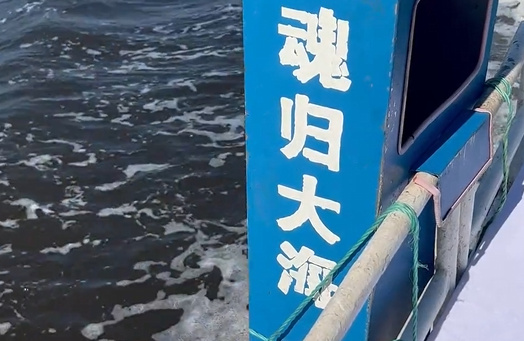
上个月特意选清晨七点来拍海晏堂,为了和老照片的光线重合。站在当年法国摄影师的位置举相机,阳光斜斜照过来,断柱上的缠枝莲忽然亮起来,像有人用画笔重新描了一遍。按下快门时,旁边走过位白发老人,举着手机说:"我小时候来,这柱子还躺地上呢,现在立起来了"。想起建国初期的修复照片:工人们用绳子拉断柱,脸上都是汗,眼里却有光——他们不是修建筑,是把散碎的历史碎片,一点点拼回去。
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海晏堂打卡照有意思:有人拼老照片和新照片,左边1870年的繁华,右边2023年的沧桑,中间缺口被二月兰补上;有人拍断柱与星空的合影,有人拍紫色花簇绕着石头的特写。去年马首回归时,博物馆展出它的新照片,旁边放着1860年的全景图——马首原来在喷泉左侧第三个位置,现在它回来了,虽然海晏堂不在了,但图片里的缺口,终于填上一块。
特意选清晨拍海晏堂那天,风掀起衣角时,旁边有位妈妈对孩子说:"你看这断柱上的花纹,和150年前的图片一模一样"。孩子仰着头问:"那它疼吗?"妈妈蹲下来,摸着断柱说:"它记着疼,但也记着我们没忘"。忽然明白,海晏堂的图片从来不是冰冷的石头,是活着的:记着乾隆年间工匠刻刀的温度,记着1860年火焰的烟味,记着1920年孩子糖葫芦的甜味,记着修复工人掌心的汗,记着每个游客按下快门时的心跳。
风又吹过来,二月兰花瓣落在相机上。望着断柱,想起有人说"照片是时间的胶囊"。海晏堂的每一张图片都是胶囊,里面装着繁华、毁灭、生机、希望。打开这些胶囊,看见的不是石头,是我们和祖先共同的记忆——比如现在我镜头里的断柱,阳光照着缠枝莲,像150年前的工匠刚刻完最后一刀,像修复工人刚把它立起来,像那个举着糖葫芦的孩子刚跑过去,所有的时间都叠在这里,变成一张能触到温度的照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