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清明,我跟着舅舅一家坐三小时高铁去青岛石老人浴场。舅舅怀里的瓷罐裹着外婆织给外公的藏青方格围巾,边角泛着旧毛边——那是外婆压在衣柜底层十年的“伴手礼”,说要带着找外公。
海边风凉,外婆的妹妹攥着佛珠念叨:“哪有不进祖坟的?祖宗找不到根。”舅舅翻出外婆的日记,夹着银杏叶的那页写着:“我蹲厨房剥毛豆时,想起二十岁跟你哥去海边,他抱我转圈圈溅得满脸海水。现在腰弯了蹲不下,可我想变成一滴水,跟着潮水跑一跑。”风掀起日记,银杏叶飘进海里,像外婆小时候叠的纸船。
撒骨灰选在退潮下午。舅舅打开瓷罐,骨灰像细雪飘进海,舅妈把外婆的老花镜轻放水面:“妈,这镜子能照见海底的鱼。”小侄女突然喊:“奶奶变成小波浪啦!”我们望着颗粒沉进蓝里,没有想象中悲伤——倒像外婆脱下穿了一辈子的旧棉服,躺进最软的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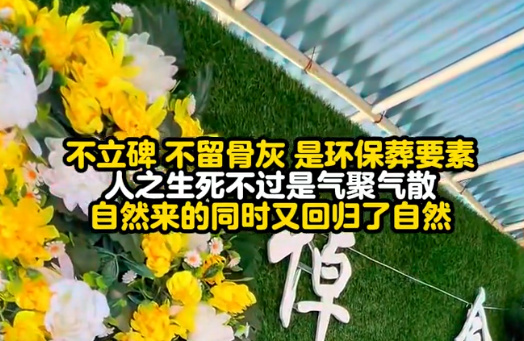
后来再去海边,我总摸一摸海水。上次张阿姨问“撒海会不会冷清”,我想起外婆日记:“海那么大,装得下所有想念,比坟头草长得还快。”现在风里的咸味儿是她晒的梅干菜,浪打脚腕的凉是她冬天捂我手的冰毛巾,退潮时的贝壳说不定是她藏的小礼物。
前几天整理遗物,翻到外婆织了一半的藏青方格毛线袜。风把毛线团吹到楼下海棠树底,我捡时突然闻到海的味道——明明离海二十公里,那股咸暖像外婆拍我肩膀:“丫头,线别缠了,我帮你理。”

原来外婆要的“好”,从不是刻在石头上的名字,是风能吹到、水能带走,能去外公跑船的所有地方,能在每阵海风里钻我衣领说“我在呢”。撒海不是消失,是她换了种方式存在——像浪从不停,想念也不断,跟着潮水漂去更远的地方,看更美的风景。
这是最舒服的结局;是最温柔的成全。人死后骨灰撒海好吗?答案藏在她日记的字缝里,藏在撒海时飘起的围巾角,藏在每一次摸海水时,手心传来的、像她温度的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