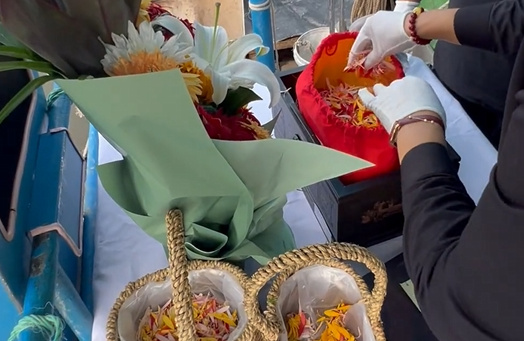清晨七点,中关村南大街的梧桐叶还沾着晨露,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铁栅栏门刚推开一道缝,沙海江的身影就挤了进去。他的白大褂下摆蹭着门柱上的青苔,口袋里装着老伴塞的鸡蛋饼,咬了一口还冒着热气——这是他三十年来不变的习惯:每天比实验室的阿姨早到半小时,先去看一眼恒温箱里的棉铃虫。实验室的灯已经亮了,恒温箱的指针稳稳停在25℃,沙海江掀开箱门,玻璃罐里的棉铃虫正沿着棉花叶爬,黑色的小脑袋晃来晃去。他掏出放大镜,眯着眼睛数虫体上的刚毛:“第三只,刚蜕皮,鞘翅还软着呢。”笔记本上的字迹歪歪扭扭,却每一笔都带着温度——这是他记录了三千多个日子的“虫类日记”。
沙海江研究的是昆虫与植物的“军备竞赛”。比如棉铃虫为什么能对抗转基因棉花?他会从棉花叶子里提取化学物质,用气相色谱仪分析成分,再把这些物质涂在人工饲料上,看棉铃虫吃不吃。“你瞧,这虫子精得很,”他用镊子夹起一只棉铃虫,指尖轻轻碰了碰它的触角,“它能通过触角上的感受器,分辨出棉花有没有‘下毒’。”去年夏天,实验室的棉铃虫突然大规模死亡,沙海江蹲在恒温箱前守了三夜。后来发现是通风口进了甲醛——装修工人误把实验室的通风管接错了。他把存活的棉铃虫单独养起来,每天给它们换新鲜的棉花叶,终于培育出了抗甲醛的品系。“生命的韧性啊,比我们想的强多了,”他摸着那只最壮的棉铃虫,像摸着自己的孩子。
沙海江在海淀住了三十年,从读研时的筒子楼,到现在的老教师楼,窗户正对着动物研究所的钟楼。周末的时候,他会带着七岁的孙女去海淀公园。孙女蹲在花坛边看蝴蝶,他就蹲在旁边,指着蝴蝶的触角说:“这是棒状触角,只有鳞翅目才有哦。”孙女摘了朵蒲公英吹,他赶紧接住飞散的种子:“别浪费,这是蒲公英的果实,每一粒都带着降落伞。”小区里的流浪猫都认识他——他总在阳台放一碗猫粮,有时候还会给猫做“体检”:“这只黄猫,牙口不错,就是有点耳螨,得涂药。”楼下的阿姨开玩笑:“沙老师,你都成动物百科全书了。”他笑着摆手:“哪有,我只是比别人多瞧了几眼。”
有人问他,做昆虫研究这么多年,腻吗?他翻出手机里的照片——那是一只刚破茧的菜粉蝶,翅膀上的鳞片还沾着晨露,阳光照上去,像撒了一把碎钻。“你看这翅膀,每一片鳞片都是六边形的,排列得比瓷砖还整齐,”他的眼睛亮起来,像个发现新玩具的孩子,“大自然的设计,比任何设计师都厉害。”去年,他的学生在《昆虫学报》上发表了论文,里面用了他积累了十年的棉铃虫数据。学生说:“沙老师,没有您的坚持,我们根本做不出来。”他摸着论文的封面,指尖划过自己的名字:“不是我坚持,是这些虫子在教我——它们活了几亿年,比我们懂怎么适应环境。”

傍晚六点,沙海江抱着实验记录走出研究所。夕阳把他的白发染成了金褐色,路过卖糖葫芦的摊子,他停下来买了一串。糖稀裹着山楂,咬一口,甜津津的,像极了他第一次发现棉铃虫触角感受器时的心情。海淀的风里飘着玉兰花的香气,他抬头望着远处的中关村大厦,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,像一片金色的海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放大镜——那是他读研时买的,镜身已经磨得发亮。“明天得给棉铃虫换饲料了,”他自言自语,脚步很慢,却很坚定。远处传来地铁的鸣笛,他朝着家的方向走去,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,像一条通向实验室的小路,弯弯曲曲,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