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风裹着咸湿味钻进衣领时,我正蹲在礁石上,把母亲最爱的桂花糕掰成细碎的小块。潮水漫过脚踝,凉丝丝的,像她生前拍我手背的温度——去年今日也是这样的清晨,我们把她的骨灰混在白菊花瓣里,顺着海浪送出去。她穿着那件藏青布衫,是攒了三个月退休金买的,说等秋天去海边拍照片,结果照片没拍成,倒成了她最后的衣裳。
最开始的日子总像缺了块拼图。玄关的鞋架上还摆着她的塑料拖鞋,鞋尖沾着上次去海边踩的细沙;厨房挂钟下贴着她写的便签:“小囡明天要吃 pancakes,记得买牛奶”;冰箱门把手上,还挂着她织了一半的毛线袜,针脚歪歪扭扭,像她笑起来皱成一团的眼角。我总忍不住摸那些东西,指尖碰到凉丝丝的塑料拖鞋,突然就红了眼——以前她总说“拖鞋要摆整齐,不然海边的风会把福气吹走”,可现在风还在,她的声音却变成了海浪的回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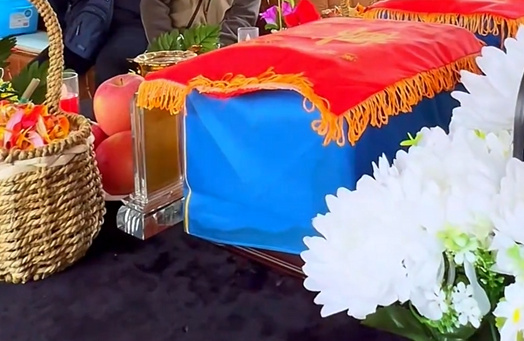
直到某天傍晚,我抱着她的茉莉花茶罐去海边。夕阳把海面染成橘红色,我掀开盖子,把茶叶倒进水里——她总说茶要“泡着海风才香”。茶叶梗在浪里打旋,突然一片桂花瓣飘过来,落在我手背上。那是上周我洒的,她生前最爱的桂香,说比香水好闻,“自然的味,贴心”。那一刻突然懂了,她没走,只是把家搬到了海里:玄关的拖鞋换成了浪尖的泡沫,厨房的便签换成了风里的桂香,连她织到一半的毛线袜,都变成了潮汐里游来游去的鱼线——原来海葬从不是“送走”,是让她变成了更辽阔的陪伴。

现在我每个月都会去海边,带的东西越来越“杂”:她爱喝的茉莉花茶,泡在透明罐里顺着浪倒下去,茶烟混着海雾飘起来,像她以前摇着蒲扇的样子;她织到一半的毛线,我续上了线,织成小袜子给邻居家宝宝,剩下的毛线缠成球扔进海里——她总说“毛线要跟着风走,才能找到新的家”;甚至孩子刚学会走路的小鞋子,我也带了一双,沾着草地绿渍的鞋尖被潮水打湿,像她以前蹲在地上给我系鞋带的模样。有次邻居问:“总去海边,不难过吗?”我笑着摇头——风里飘来桂香时,我知道是她在说“小囡,今天的茶泡得刚好”;浪拍礁石的声音响起来,我听见她在唱以前哄我睡觉的儿歌,比以前更轻,却更清楚。
上周孩子举着画本跑过来,画里是穿藏青布衫的老太太,站在海浪里,手里举着桂花糕。“外婆在给我们送吃的!”孩子歪着脑袋说。我蹲下来摸他的头,看见画本上的海浪涂成了淡蓝色,像母亲生前织的毛线团。突然想起她去世前说的话:“等我走了,就去海边。那里的风最柔,能吹到你们每一个角落。”原来她早就选好了“家”的模样——不是冰冷的墓碑,是会呼吸的海浪,是会飘香的桂花瓣,是会跟着风跑的毛线球。
现在我煮糖水蛋时总会多放一勺冰糖,那是她的习惯,说“甜一点,日子才会软和”;晒被子时会把被单往风里抖一抖,像她以前那样,说“把海的味道收进被子里,晚上睡觉才踏实”;甚至逛菜市场时,看见卖桂花糕的摊子,总会多买一盒——一半留给自己,一半装进玻璃罐,带到海边。风掀起罐子的盖子,桂香飘出去,落在浪尖上,我知道她会接住,像以前接住我掉在地上的玻璃弹珠那样,小心又温柔。
海葬从不是结束,是母亲给我们的“延迟告别”:她把自己变成了生活里的每一阵风、每一片云、每一朵浪花,变成了孩子画里的老太太,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