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风裹着咸湿的味道钻进衣领时,我正蹲在海边的礁石上,把妈妈最爱的桂花糕轻轻掰成小块。去年今天,也是这样的风,我们把她的骨灰和着花瓣撒进海里——那时我以为,从此就没有了“祭拜”的地方,直到海浪卷着糕屑慢慢沉下去,我忽然听见风里传来她的声音:“慢点儿,别把糕渣弄碎了。”就像我小时候蹲在厨房门槛上,看她揉面时说的那样。
其实很多人问过我,骨灰撒海后,怎么“供奉”先人?我想说,供奉从来不是摆一桌冷菜、烧一沓纸钱那么简单。它是藏在生活缝隙里的、带着温度的小秘密——就像我家茶几上永远摆着妈妈的白瓷杯,杯沿有她当年嗑瓜子留下的小缺口。每天早上我会倒一杯温水,放在杯垫上,就像她还在客厅里织毛衣,抬头说“我的水凉了,帮我换一杯”。晚上煮面时,我会多煮一把,盛在她的蓝花碗里,放在厨房的窗台上。蒸汽飘起来,模糊了玻璃上的窗花,我忽然觉得,她就站在我旁边,闻着面香说“放点儿醋,你小时候最爱吃醋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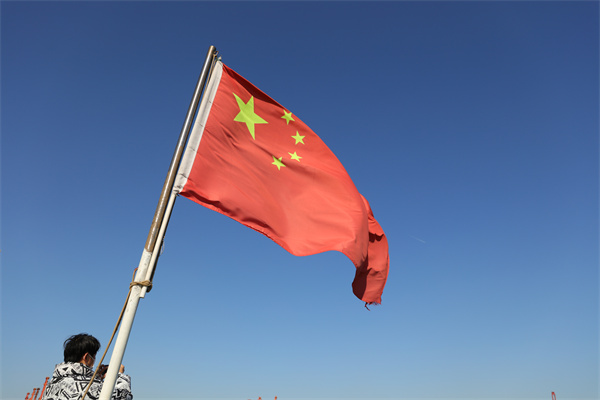
有人说,没有墓碑,是不是就“没根”了?可我觉得,根从来不是一块刻着名字的石头。去年春天,我带着儿子去撒海的海边,捡了几个带着螺旋纹路的贝壳,装在玻璃罐里。儿子问:“奶奶在贝壳里吗?”我摸着他的头说:“奶奶在海里,贝壳是她给你的礼物。就像奶奶当年教我捡贝壳,说‘每个贝壳里都藏着海的声音’。”现在儿子每天放学,都会趴在玻璃罐前听“海的声音”,有时候会说:“妈妈,奶奶说她喜欢我画的画。”我知道,他记住的不是“奶奶在海里”,而是“奶奶爱我”——就像我记住妈妈当年教我织围巾的针法,记住她总把我的衣领翻好,记住她那句“人要笑着过日子”。
上个月整理旧物,翻出爸爸的木工工具箱。他当年是厂里的木工,总帮邻居修桌椅,工具箱里还留着他磨得发亮的凿子。我把工具箱擦干净,放在阳台的架子上。周末的时候,我学着他的样子,给儿子修玩具车。螺丝刀拧下去的瞬间,我忽然想起爸爸当年教我用凿子:“手腕要稳,劲儿要匀,就像做人一样。”那天晚上,我做了爸爸最爱的红烧肉,多盛了一碗放在工具箱旁边。儿子凑过来闻:“爷爷爱吃红烧肉吗?”我点头:“你爷爷做的红烧肉,肥而不腻,我小时候总偷着吃。”儿子说:“那我以后要学做红烧肉,给爷爷留一碗。”我忽然红了眼眶——原来,供奉不是“给先人什么”,而是“把先人给我们的,传下去”。

昨天傍晚,我又去了海边。夕阳把海面染成金红色,海浪拍着礁石,像妈妈当年拍我后背哄我睡觉的节奏。我摸出手机,播放爸爸当年的语音:“丫头,天气预报说要下雨,记得带伞。”风把语音吹得飘起来,我忽然觉得,他们从来没有离开——妈妈在桂花香里,爸爸在木工凿子的纹路里,他们在我给儿子织的围巾里,在儿子画的画里,在每一次我笑着说“我很好”的时候。
骨灰撒海,不是“消失”,是“回家”——回到他们最爱的自然里,回到我们最真的生活里。供奉从来不是“仪式”,是“记得”——记得他们的味道,记得他们的习惯,记得他们教我们的道理,记得他们爱我们的样子。那些爱我们的人,从来没有离开,他们在风里,在浪里,在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里,永远活着,永远笑着,看我们越来越好。
